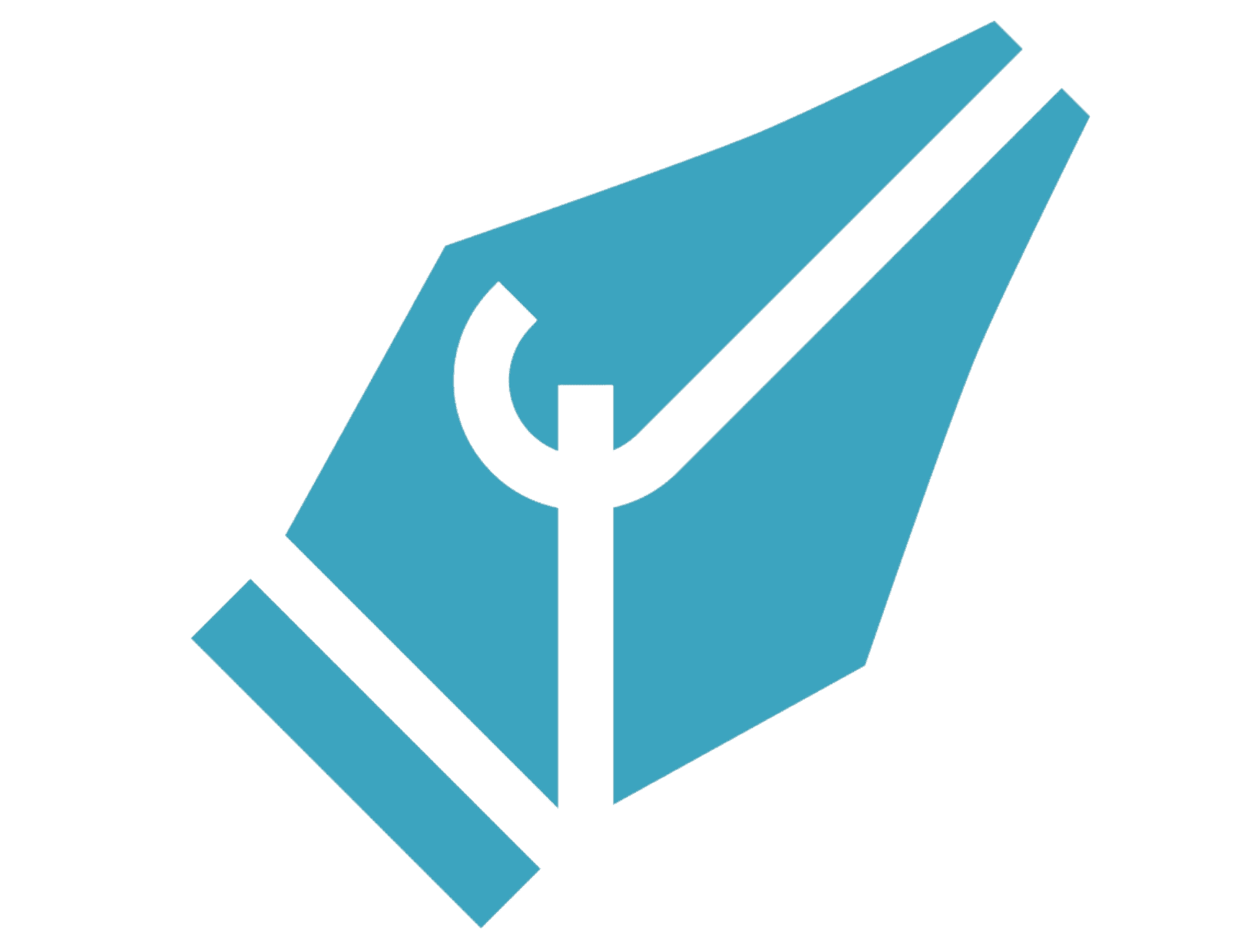研究中國,常常像是在一個半透明、半封閉的房間裡觀察光影變化。看不見全貌,只能從縫隙裡捕捉訊號。對研究者而言,中國新聞不只是資訊傳播的載體,更是觀察權力變動、政策走向與政治氛圍的重要窗口。尤其每年「兩會」期間,北京釋出的每一則新聞、每一份文件、每一個版面安排,都像是一套經過精密設計的語言系統,等待外界解讀。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副主任洪耀南博士以自身長期研究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背景出發,指出自己看新聞,更多是從讀者的角度切入。
中國政治體制高度封閉,很多關鍵變化無法直接觀察,因此新聞就成為最重要的外部切口。對中國研究者來說,真正值得注意的,往往不是表面新聞本身,而是新聞背後想傳達什麼、刻意不說什麼,以及哪些變化和過去不同。
從版面與缺席名單,看中國權力結構的變化
在中國的新聞系統裡,版面從來不只是排版問題,而是權力秩序的可視化。過去中共仍強調「集體領導」時,政治局常委的照片大小相對一致,象徵領導班子的整體性;但到了習近平時代,這種視覺安排逐漸改變。尤其十九大、二十大之後,其他政治局領導人的存在感明顯淡化,習近平一人居於絕對中心,其他人彷彿只是圍繞核心運作的幕僚群。若說過去總書記是「班長」,那麼如今的習近平更像是「班主任」,整體體制早已從集體協調走向定於一尊。
同樣值得注意的,還包括兩會代表的異常缺席。這次兩會有113名代表遭除名或未出席,在2,756名代表中接近5%。這不是一個可以輕忽的小數字,而是一個明顯的政治訊號。對中國研究者來說,這種異常消失往往代表整肅、失勢,或某種內部調整正在發生。中國政治不會把答案直接說出來,但它會用「誰不見了」來暗示問題所在。

筆名、用詞與消失的十四天:中國新聞的訊號學
中國官方新聞有一套成熟的符號系統,其中最經典的就是筆名體系。例如「任仲平」代表中共中央重要政論立場,是為黨路線定調的權威聲音;「鐘聲」多用於國際新聞與外交表述;而近年出現的「鍾才文」,則與中央財經委員會的政策意志有關。對外界而言,這些筆名不是文學趣味,而是辨識政策層級與政治訊號的重要工具。
除了筆名,新聞用詞的變化也常被拿來做為判讀依據。例如對台工作會議中的措辭是否從「堅持」變成「深入」,是否從「反對」變成「堅決反對」,都容易引發外界高度關注。不過講者提醒,真正重要的並不只是單一字詞,而是它放在什麼場合、出自哪一份文件,以及是否位於更高層的對台工作會議脈絡中。若離開大框架,只抓個別字眼,往往容易過度解讀。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習近平曾有十四天未公開露面。這段時間一度引發各種傳言,甚至有人猜測是否發生政變。但後來習近平公開接見白俄羅斯總統,外界研判更可能是身體因素,甚至不排除曾接受某種手術。這顯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健康狀況,已成為各國高度關切的情報項目。從APEC到國際接待細節,各國都在觀察習近平的行動、體力與公開表現。這也意味著,未來他出席國際場合的頻率可能會進一步下降,除非是以中國為主場的高度可控環境。
兩會真正的重點:經濟放緩與「十五五」布局
中國每年春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政治議程,因此也被視為觀察中國政治與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兩會表面上議題繁多,但洪耀南認為,真正的核心還是在經濟。尤其這次 GDP目標被認為可能落在4.5%到5%之間,這是極具指標性的訊號。胡錦濤時代中國經濟成長率曾高達10%,習近平上台以來則大多維持在較低區間,如今再往下調整,說明中國經濟持續走緩已是不爭事實。
更關鍵的是,中國當前的經濟並不是全面衰退,而是出現了明顯的「K 型化」:外銷依然強勢,甚至貿易順差突破一兆美元,但內需疲弱、消費不振。這意味著中國經濟表面上還能維持漂亮數字,內部卻已出現結構性失衡。洪耀南甚至以「布里茲涅夫式停滯」形容習近平當前面臨的經濟階段,也就是總體看似穩住,實則難以再突破。
接下來值得密切注意的是「十五五規劃」,因為這不只是一般五年計畫,而是直接連接到2035年這個關鍵時間點。中國提出到2035年要讓人均所得「翻一番」,目標上看兩萬五千美元。若從GDP成長來推算,每年需要維持相當高的增幅,實現難度極高。因此洪耀南認為,中國未必能完全靠實質經濟增長達標,而更可能藉由人民幣升值、統計口徑調整等方式來逼近目標。近來中國學界不斷出現「人民幣被低估」的說法,也可視為這條政策路線的鋪墊。

習近平的戰略想像:2035、2049與中國式現代化
若要理解中國的內政、經濟與對台政策,關鍵仍在於理解習近平「在想什麼」。洪耀南指出,習近平近年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不是一句空泛口號,而是整套戰略認知的基礎。他認為國際權力結構正在重組,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相對優勢下降,中國則站在崛起機會之上。
在這種敘事下,習近平提出「中國式現代化」,並不把現代化理解成制度自由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或文明演進,而是更偏重科技能力、國家動員與制度控制。他認為中國不必複製西方模式,而要走出一條由黨主導、國家統籌的現代化道路。2035年,是他心中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完成的重要節點;2049年,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目標。
在這個時間框架下,台灣問題也被重新放置。鄧小平時期對台基本路線是「可以拖」,這一代解決不了,就留給下一代;但習近平在2019年「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談話中,已明確表達「台灣問題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這代表他的對台論述與鄧小平時代已經出現明顯切割。不過,這並不等於他一定會在短期內動武。從習近平自身權力穩定角度來看,他並不需要透過攻台來鞏固連任,相反地,一旦開戰反而增加政治風險。因此,那種「2027 為了連任而攻台」的說法,在邏輯上並不成立。
對台時間表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內部治理與軍權清洗
當外界談論中國對台政策時,往往容易把一切變化都直接聯想到戰爭準備,但講者提醒,很多中國內部權力整肅的首要原因,其實未必是台灣,而是體制內部治理與權力控制。例如張又俠事件,就被部分媒體簡化為「習近平想打台灣、張又俠反對」,但講者認為這種解讀過於粗糙,甚至邏輯不通。對習近平來說,政權穩定一定比對外冒進更重要。
真正需要看到的是,習近平這些年已逐步改造整個權力運作機制。他打破過去鄧小平時代所建立的任期、接班與集體協調慣例,改由自己親自面試重要人選,讓政治局、軍方高層乃至各級幹部形成一套由上而下的個人效忠體系。這意味著,如今中國並不存在一個足以與習近平正面抗衡的「反習中央勢力」,真正活躍的更多是下面的小派系、小圈子,彼此卡位、競爭、等待上升機會。
軍方也是如此。解放軍近年持續清洗,不只是因為貪腐問題,也涉及指揮體系、派系平衡與忠誠審查。軍中出缺嚴重、重要職位久懸未補,顯示不是單純的人事空窗,而是體制內部在重新洗牌。從這個角度看,觀察中國軍方異動,與其急著推論是否攻台,不如先理解它是否反映出更深層的治理焦慮與權力重整。
讀中國新聞,真正要讀的是背後的結構
整體而言,洪耀南透過兩會、筆名系統、新聞版面、經濟目標、對台論述與軍方異動等多個面向,提醒大家:閱讀中國新聞,不能只看表面事件,而要回到整個政治結構與權力邏輯去理解。中國新聞從來不是單純的新聞,它既是宣傳、也是定調,更是有限但重要的情報來源。
在這個高度封閉的體制中,研究者能做的,不是期待一次讀懂全部真相,而是不斷從細節中拼出輪廓:誰出現、誰消失、誰發言、誰用什麼筆名、哪個詞被強調、哪個目標被反覆重申。這些看似瑣碎的訊號,其實正構成理解中國最關鍵的地圖。
而放在今天的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脈絡下,這樣的解讀能力不只是學術訓練,更是一種現實判讀的基本功。
本文以AI工具依現場錄音檔製作摘要,並經人工審閱、修訂完成
(紀錄整理:孫璇;編輯:邱家宜)
廣告
本次講座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