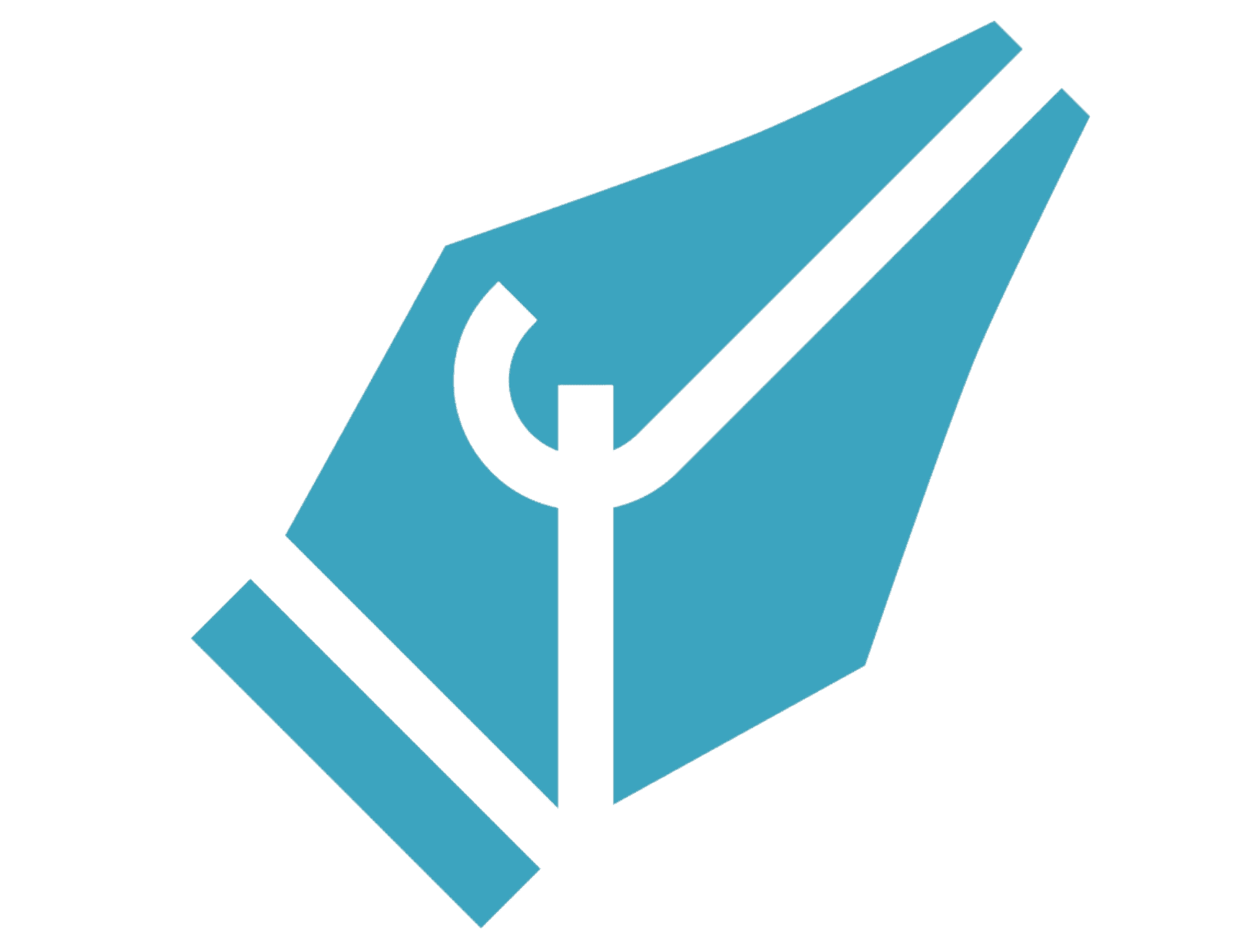提案說明
提案人 –
楊智強

失根的羅興亞:迫害、剝削、顛沛流離
愛上佛教徒的羅興亞人:「在若開邦裡我們不可以能在一起,所以選擇離鄉背井。」搭偷渡船到馬來西亞的羅興亞人:「馬來西亞的老闆都扣著我們薪水,沒辦法、所以我才再跑。」15歲偷渡出緬甸、現為人蛇的羅興亞人:「若家鄉狀況許可,我當然想要回去啊。」、在泰緬邊境討生活的羅興亞人:「你們很幸運不是羅興亞人,想去哪就可以去哪…」
每一位羅興亞人都有自己為什麼逃離家園的故事,甚至有些人必須一逃再逃,不斷冒著風險前往另一個想像中的國度。因為歷史因素沒有國籍與護照的羅興亞人,每次遷移都無法循正當管道入境,必須透過人蛇集團的安排偷渡入境。除了成功抵達目的地的人之外,有為數不明的人們被拐騙賣給罪犯、淪為娼妓或奴隸,有的人甚至喪命途中。羅興亞人在這個南亞與東南亞大陸與島嶼之間無止境的流浪,至今、每天都仍在上演。

議題背景:
居住在緬甸西南部若開邦的羅興亞人,從70年代開始斷斷續續的遭到緬甸政府侵擾與迫害,並且在1982年剝奪了他們原有的公民身份,讓羅興亞人成為了無國籍者。在2012年一次大規模的地方衝突之後,羅興亞人被緬甸政府強迫遷至散落在若開邦各地的「難民管制區」,限制自由。至此,羅興亞人受到的迫害與歧視越來越頻繁,因此開始大量逃離家園。
2015年經過外媒的調查報導,揭發了在泰國東南部人蛇集團的巢穴,並且發現許多羅興亞人被監禁在此,甚至在當地發現百人塚,證實有許多希望靠人蛇從緬甸偷渡到馬來西亞的羅興亞人,遭到人口販子綁架勒索、甚至殺害。2015年後,從緬甸若開邦搭船到泰南後進入馬來西亞的路線遭到泰國軍警大力查緝,為了躲避風頭,人蛇的蹤跡越來越少。
但在緬甸家鄉的迫害羅興亞人的事件仍在發生,甚至在2017年8月底爆發了緬甸軍警大規模迫害羅興亞人的慘劇,讓將近70萬的羅興亞人逃至孟加拉的科克斯巴札爾的難民營。剛開始孟國因為人道精神接納難民,但時間一久孟加拉社會開始出現排斥,而緬甸若開邦的家鄉也早已付之一炬,他們的未來是一片茫然。

採訪動機:
2017年11月到12月,本採訪團隊(Loop Media Team)前往泰國與孟加拉難民營採訪羅興亞人在當地的狀況時,發現到雖然海上的偷渡路線已經被封閉,但從陸路偷渡的狀況仍然相當頻繁,甚至在這條長遠的偷渡路程中,有更多的羅興亞人遭到利用、性侵甚至殺害。因此採訪團隊決定將羅興亞人的新聞採訪時間拉長,並且在2018年中與年底再度前往相關地點,更深入採訪這條苦難的流浪路線。

採訪計劃:
全程採訪計畫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去年底,採訪團隊前往泰國與孟加拉科克斯巴札爾難民營實地了解羅興亞人在各地的情形,並將難民營中的狀況帶回台灣。第二階段為2018年4月到5月的時間,採訪團隊透過追蹤幾個家庭與個案的方式,除了紀錄口述經歷之外,也會跟著個案與人蛇集團交涉並且了解偷渡的過程與細節,希望可以抽絲剝繭出犯罪集團的結構。第三階段暫定為2018年10月到11月,無論採訪個案/家庭偷渡成功與否,再度前往所在地進行採訪。近一步了解成功偷渡後,他們的生活是否改善?

2017年11月至12月,採訪團隊前往泰國與孟加拉。(已完成)
2018年4月中至5月底,採訪團隊三人一同前往泰國與孟加拉。(進行中)
2018年10月至11月,採訪團隊一同前往緬甸、泰國與馬來西亞。(規劃中)

Loop Media Team採訪團隊:
文字記者 – 楊智強
簡歷:《報導者》特約記者、《經典雜誌》特約記者、公視《獨立特派員》特約記者。
進入蘇丹與南蘇丹製作內戰專題;羅興亞在若開邦、孟加拉、泰國等地系列專題;多次進入韓國、中朝邊境等地製作韓國相關新聞專題;在印尼製作雅加達省長大選與移工專題;在台灣製作「廢墟少年」專題等豐富新聞採訪經驗。
平面攝影記者 – 張俊熙(Junhee Jang)
簡歷:韓國《時事IN》週刊特約攝影記者、日本《朝日新聞》特約攝影記者、美國《時代》雜誌特約攝影記者、UNHCR克倫族難民專題在韓特約攝影記者。
多次進入泰緬邊境拍攝克倫難民專題、並受聯合國難民總署特聘為2017年度專題攝影記者;以巴衝突新聞專題攝影;緬甸克欽族內戰新聞專題攝影;阿富汗與巴勒斯坦反恐戰爭專題攝影;敘利亞難民潮跨越歐亞專題追蹤攝影等豐富海外新聞攝影經驗。
影像攝影記者 – 郭若瑀
簡歷:荷蘭《Zoomin.TV》特約動態攝影師、《IKEAXPaper》廣告動態攝影師、《旅讀雜誌》特約平面攝影師、《世界公民島雜誌》特約採訪記者
深入探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採訪和平機構促進交流;進入中國新疆拍攝維吾爾族紀實短片;進入中國西藏與藏南地區採訪拍攝藏族氂牛製品社會企業,線上發表甘南與西藏攝影集。
Report
正式報導
被連根拔除的民族》當孟加拉用「杜特蒂式掃毒」對待羅興亞難民:他們是毒害幫兇、抑或是代罪羔羊?
面紗遮掩下只露出深邃雙眼的羅興亞人奴爾(化名),深色伊斯蘭罩袍除了蓋住了全身之外,也掩護了她心中的緊張。手中拽著一張偽造的孟加拉身分證,她搭著摩托嘟嘟車準備離開羅興亞難民營。而這股發自內心的不安並不是來自手中的假證件,而是綁在右腿上的一個長方形塑膠包裹,裡面裝的是惡名昭彰的毒品,鴨霸(Yaba)。
司機連珠砲的叫罵、此起彼落的喇叭聲、垃圾腐敗的味道還有忽然降下的傾盆大雨,庫圖帕朗(Kutupalong)難民營市集的混亂成了各種犯罪的保護色,讓人不易發覺。混在一般嘟嘟車乘客中間的奴爾,在檢查哨警察不耐煩的情緒下找到漏洞鑽出管制區,帶著毒品進入鄰近的小鎮科克斯巴札爾(Cox’s Bazar)。
「我需要錢,所以我答應幫他們運毒。」簡單明瞭的自白表達了奴爾心中的無奈。現年27歲的她,6年前舉債讓丈夫偷渡到馬來西亞。她原本以為可以靠著丈夫寄回來的錢過好生活,但沒想到丈夫居然斷了音訊不聯絡。面對大筆債務與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她一度萬念俱灰。 但就在跌入絕望的谷底之前,惡魔伸出手,拉了她一把。 為了還債,奴爾開始在市集上販售國際組織分配給家人的食物配給。窮困潦倒的狀況也讓奴爾被毒販盯上,吸納她成為運毒的「工具」。
一位匿名的孟加拉毒販指出,鴨霸有不少種類,在科克斯巴札爾中最受歡迎並且「品質」最好的鴨霸是以葡萄牙球星為名的「羅納度7號」(Ronaldo 7),目前市價是一顆250塔卡(約90台幣)。奴爾走私出來的長方形包裹一包約5千顆,市價則是125萬塔卡(約45萬台幣)。
奴爾並不曉得一包鴨霸市價多少,她只曉得每運送一次可以收到6千塔卡(約2100台幣)的酬勞,而這些錢可以大幅改善家庭的窘境。「我很感激幫我介紹這個工作的人,沒有他,我們一家人會活不下去。」但相對於奴爾的「感謝」,對毒販來說,她只是一個可被拋棄的棋子。毒販在奴爾運毒的過程中會租另一台嘟嘟車跟在後方,若她身上的毒品被檢查哨的警察查獲,毒販會馬上掉頭離開,撇清關係。
訪談結束後奴爾卸下原本緊張的神情,跟一位身穿學校制服、年約10歲的男孩交談。奴爾也熱心的跟我們介紹小男孩就是她的二兒子。「我不會奢求他們有什麼成就,能受到好的教育就夠了。」奴爾雙手環抱著男孩,說出了她心中最卑微的期盼。

(攝影:Junhee Jang)
這一刻,她只是位深愛孩子的母親。
在羅興亞人身上,毒販看到可以利用、剝削的機會。而孟加拉政府,同樣也在羅興亞人身上看到了可施力的支點,企圖扭轉總理低迷不振的支持度以及年底的選情。
反毒戰爭下的代罪羔羊?
今年5月14日,孟加拉總理謝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向全國發表演說,表示國家開始掃毒行動,並指出毒品就是從緬甸與孟加拉邊境的特克納夫(Teknaf)流入,開始在邊界大舉清掃,並逮捕、處決了許多羅興亞運毒者。孟加拉遭到毒品危害已久,社會弊病叢生讓人民對毒品深痛欲絕,所以大眾普遍傾向支持這種「杜特蒂式」的掃毒行動。
但這個行動背後的意圖與手段受到人權團體的質疑。
「將毒品在孟加拉肆虐的原因跟羅興亞難民做連結,是錯誤的。」孟加拉人權組織Odhikar的秘書長阿迪魯爾(Adilur Rahman Khan)反對政府將毒品問題的責任推給羅興亞人,並且點出腐敗執法單位以及跟毒販掛勾的官員才是應該被咎責的對象。他認為有許多孟加拉知名的毒品教父因為有良好的政治人脈,所以才沒有遭到逮補。
阿迪魯爾所屬的Odhikar以及國際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 Watch)等指控孟國政府,放任特別警察(Special Branch)與惡名昭彰的快速行動營(Rapid Action Battalion, RAB)濫捕或甚至法外處決(Extra Juditial Killings)大量政治異議人士。而像是奴爾一樣遭到毒梟利用的羅興亞人,則成了政府向民眾邀功與合理化濫殺的「反毒成果」。「抓那些小魚根本沒有真的在掃毒,這場戰爭的政治意圖大過反毒!」阿迪魯爾說。
然而,這並不是孟加拉政府第一次操作羅興亞難民的議題。
去年8月25日緬甸軍方對羅興亞人的迫害發生之後,為數70萬的羅興亞人陸續跨越邊境來到孟加拉。採訪團隊12月來到科克斯巴札爾時,街道上不時可以看到孟加拉總理哈西娜的宣傳標語上寫著「人道之母」(Mother of Humanity)幾個字,強烈感受到孟國政府希望塑造哈西娜之於羅興亞難民議題仁慈的形象。
但諷刺的是,在緬甸若開邦的迫害剛開始時,孟加拉政府最初的決定維持封鎖邊境的政策,不讓羅興亞人入境。「是後來孟加拉的NGO與人民施加壓力,才讓政府轉變態度。」阿迪魯爾認為孟加拉政府從人道危機爆發開始,到現在的反毒戰爭,都在利用羅興亞議題來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
「反毒戰爭」在幾個月來,以受爭議的手段在全國雷厲風行的掃蕩下,毒品輸入最前線的緬孟邊境地區情勢也變得越來越緊張。在這裡,除了反毒行動的槍戰外,也有地方勢力與羅興亞難民之間的衝突與謀殺。再加上去年8月緬甸若開邦的屠殺發生後,孟加拉邊境的烏奇亞(Ukhiya)與特克納夫等地區的羅興亞人與孟加拉人比例出現2比1的翻轉,讓情勢更加惡化。
人口比例的變化對於當地孟加拉居民而言有相當大的衝擊。從小到大跟朋友與鄰居一起生活的家鄉在短時間內湧入了大量陌生人,以及政府口口聲聲對外宣稱這些陌生人就是製造社會動盪的來亂源之一,這些因素導致了居民對羅興亞難民產生負面印象,甚至開始在羅興亞難民身上被貼上了犯罪者的標籤,恐懼與不信任氣氛導致了兩邊的關係每況愈下。
「透過讓孟加拉居民還有羅興亞人的共同參與行動劇演出,讓雙方更了解彼此。」孟加拉人權組織Ain O Salish Kendra(ASK)的專案協調主任阿布阿赫曼(Abu Ahemed Faijul Kabir Farid)指出,ASK在科克斯巴札爾的辦公室特別組織團隊與招募志願者,針對這個議題召開了不少工作坊跟課程,試圖減緩雙邊的緊張關係。
「但我們怎麼說還是個小型NGO,要消弭這樣的敵意,只有我們來做是完全不夠的。」阿布阿赫曼點出了孟加拉政府與社會面對羅興亞難民相關議題消極的態度。另外,ASK也提供法律相關知識與技術的援助,希望讓羅興亞人跟孟加拉人在面對司法問題時可以得到平等的對待,但是阿布阿赫曼也承認,現實狀況跟理想中平等的目標相比,還有很大一段差距。

(攝影:Junhee Jang)
淡去的人道與漸濃的排外
因為邊界地區的總人口大幅上升,當地的物資出現供給失衡的狀況,導致了當地的消費水準大漲。甚至有不少願意領取低薪的羅興亞人溜出難民營到科克斯巴札爾的商家工作,讓當地人感到工作機會減少,這些變化都讓孟加拉社會裡接納「同胞」的人道主義呼聲漸弱,轉變風向,排除「麻煩製造者」的聲音則是越來越響。
「你過來!你是從哪來的?」接受匿名採訪的高階警官安華(化名)大聲質問一位在餐廳內工作的羅興亞員工。「我是巴魯卡里營區來的(Balikhli Camp)。」被質問的羅興亞人怯生生的承認自己的身份,安華冷笑了幾聲、揮揮手要他離開:「你看,這樣跑出來非法打工的狀況到處都有。」高高在上的態度透露了安華如何看待羅興亞人。但因為他的職位使然,他的看法對孟加拉政府在羅興亞事務上,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安華是2017年8月底羅興亞危機爆發後孟加拉中央政府特命授權的警官,他帶著一支十人的高階特警組織在科克斯巴札爾進行各種犯罪調查與監視,定期向中央政府報告並且給予建議。安華對於孟加拉政府現今對羅興亞難民議題的處理態度感到不滿,他認為政府並沒有像他一樣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相信我,若政府沒有改變態度,這裡的狀況會越來越糟!」一邊吞吐著濃濃的孟加拉香菸,一邊啜飲加入好幾匙砂糖的紅茶,操著流利的英文的安華,舉手投足顯示出他身份的顯赫。他自豪地宣稱自己是孟加拉的愛國者,所作所為都是要為國家除去「弊病」。「在接下來兩個月的時間裡,處理羅興亞議題不會再由當地政府管理,中央政府會派一個特警排來這裡接管。」安華說出這個消息時臉上帶著驕傲,因為這個決定是由他一手催生。
「現在已經有6千個逃出營區的羅興亞人被抓回來了,但我相信這只是逃跑總人數的10%而已。」安華認為從難民營逃出、進入孟加拉的羅興亞人除了涉及人口販運以及毒品外,他還認為羅興亞救世軍(Arakan Rohingya Salvation Army, ARSA)已經在難民營中招兵買馬,並且企圖滲透孟加拉國防。
無論安華的指控是否空穴來風,他對於羅興亞人的態度反應了大多數保守孟加拉社會的聲音,他們認為羅興亞人就是各種犯罪的來源。安華甚至希望政府效仿川普築起圍牆,將羅興亞人跟孟加拉社會,嚴密隔離。
但若安華的提議被政府採納,那這個狀況跟待在飽受不平等待遇的若開邦難民管制區裡,有什麼不同?
歪斜的木頭支撐著竹子搭建起的屋頂,簡陋的避難所隨時都有倒塌的可能。狹小的空間裡,無處可去的羅興亞人或蹲或站在屋簷下躲雨。不到幾公尺外,混雜泥土黃澄澄的洪水在他們面前咆哮。在滂礡大雨下,羅興亞人像是暴風海洋上載浮載沉一葉扁舟,隨時可能被巨浪吞噬。羅興亞人逃出了緬甸若開邦的難民管制區之後,原以為已經自由、被接受,但沒想到另一個名為「歧視」的牢籠仍禁錮著他們。他們來到異鄉寄人籬下,再多的懷疑眼光、歧視言語與敵視的態度,全部都只能往肚裡吞。面對無論是人為的剝削或是大自然的災害侵襲,他們只能逆來順受。
每年孟加拉從5月開始一直到10月的季風暴雨(Monsoon Season),正在無情的摧殘著散落在緬孟邊境地區的13個羅興亞難民營。根據聯合國難民總署(UNHCR)在3月的電腦模擬災害測試結果顯示,若沒有妥善準備,難民營內將會有10萬到20萬人面臨危險。
因為這是一個可預見的天然災難,孟加拉政府與國際組織協力合作,重新安置了部分營區內的難民,並且構築一些防禦工事,防止雨季帶來的洪水與泥石流威脅到羅興亞難民的生命。
根據聯合國難民總署(UNHCR)今年8月出版的報告指出,從3月的模擬評估出爐後,41,700位被評估居住在高危險泥石流地帶的居民中,已經有23,330被遷移到28個新的住所。並且計劃建設的60英畝(約24公頃)防禦設施,已經有80%完成。另外,還有32公里的磚石道路已經完成建設、2,172座臨時橋樑成功搭設。而這些防範季風豪雨的措施也成功的減少了難民營內的生命損失,相較3月預估的數十萬人受災,損害的程度有被控制。

(攝影:Junhee Jang)
但難民營面對雨季的挑戰不只有看得見的洪水與泥石流,還有跟著衍生而來的各種疾病,也是可預見的災難之一。
幾聲虛弱的咳嗽與氧氣瓶發出嘶嘶聲讓病床區有種令人害怕的靜謐,羅興亞小孩癱軟的手臂在母親的膝上顯得懨懨一息,微弱的求生意志仍透過失去光芒的眼神吼了出來。除了淡淡的藥味之外,這間診所內還充滿著一種濃烈的味道,它的名字叫做「絕望」。
牆上斑駁的痕跡可以看出來診所內長期被濕氣籠罩,排隊的病人在診間外靜靜的等後指示。幾位婦女見到外國人採訪團隊到來,好奇的多看兩眼,隨即回到寂靜的等待輪迴中,疲倦、了無生氣。
位於庫圖帕朗營區入口附近的孟加拉民間醫療組織Gonoshasthaya Kendra(GK)腹瀉治療診所中,大家正為雨季帶來的疾病忙碌,阿克利馬(Aklima Khatun)醫生也是其中之一。「雖然目前雨季還沒有帶來太大的影響,但是生病的人數有上升。」面對隨時可能爆發的疫情,阿克利馬表示GK的快速反應小組隨時都在待命。「若有狀況發生,他們可以即時反應。」
雖然國際組織與孟加拉NGO有做好準備迎接這個看不見的敵人,但資源以及人力仍相當有限。尤其是在人口將近一百萬的難民營中,來自世界各國大大小小的NGO之間要跨越語言、文化、專業以及偏見的障礙,協力合作對抗這個無孔不入的威脅,需要的是一個看得到全局的組織,或是說一個看得見問題的領頭羊。
在這裡,WHO世界衛生組織自然而然的接下了這個重擔,而WHO的羅興亞危機首席顧問埃吉爾(Eigil Sorensen)面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難民營,他認為國際社會完成了急難救助的任務,但接下來的發展仍沒有妥善的規劃。

(攝影:Junhee Jang)
人道援助戰略上的轉變
雖然孟加拉與緬甸在去年11月已經簽署備忘錄要將羅興亞人送回緬甸,但也因為這份備忘錄沒有時間表,各種相關配套措施都沒有被提及,讓羅興亞人返鄉之路遙遙無期。然而,不少駐紮在難民營的人道救援組織仍屬於緊急救難性質,並沒有長時間留下來救助的打算。「今年會有NGO開始撤出這裡,我們要做的就是確保他們的工作有人接手。」埃吉爾認為WHO除了要接續離開的NGO提供的醫療服務之外,也要開始計畫一些較長期的衛生規劃。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在5月的報告指出,羅興亞難民營中每天平均有60個嬰兒出生。「營區內能得到到衛生、乾淨接生服務的孕婦只佔了22%。」埃吉爾點出了營區內因為高生育率而必須面對的問題。
相較去年底人道危機爆發時,難民營需要的大量基本醫藥、診斷服務或是緊急手術等工作,經過了一年的努力,這些需求已經得到一定程度供給。但面對如接生等較複雜且需要長時間觀察的服務,營區內仍相當匱乏。埃吉爾也指出,尤其這些設備與人力需要大量的金錢支撐,才可能持續。
「我們談論的是一百萬人每天的衛生醫療需求,這是筆很大的數字。而我們現在連明年的經費在哪裡都還不知道。」埃吉爾說,雖然雖然7月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跟亞洲開發銀行(Asia Development Bank, ADB)等國際組織都承諾提供資金,但許多細節都還沒有被討論,讓他感到焦慮。
在羅興亞難民的議題上,國際社會除了在投入難民營內的資源不夠之外,對緬甸政府的暴行也只停在口頭譴責的層面,並沒有實質的制裁被執行。也因為國際社會對於羅興亞人的議題重視程度不足,讓緬甸政府更無忌憚的火上加油,對自己犯下的暴行完全沒有悔意。
今年四月國際刑事法庭的檢察官班索達(Fatou Bensouda)向法庭提出申請,希望調查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是否有權介入調查緬甸涉及「危害人類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雖然緬甸不是國際刑事法庭的成員國之一,但因為這個迫害的過程涉及孟加拉與緬甸兩國,屬於跨國犯罪,國際刑事法庭可能可以透過起訴孟加拉來調查此案件。國際刑事法庭也在6月要求緬甸政府作出回應。
一般以為緬甸政府會以「不回應」的方式漠視國際刑事法庭的要求,沒想到緬甸政府居然做出正面反擊,批評指控。
「羅興亞案件調查的請求沒有意義,應該取消。」緬甸政府在8月9日發布新聞稿,正式拒絕了國際刑事法庭對羅興亞迫害事件的調查請求。如此猖狂的態度讓羅興亞人尋求正義的希望之光,更加黯淡。
同樣在8月的時候,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也出版了一份名為《孟加拉不是我的國家》的實地調查報告,顯示現在在羅興亞難民營內,平均每人可使用的空間只有10.7平方公尺,遠低於45平方公尺的國際標準。而孟加拉政府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居然要將20萬羅興亞難民遷移至吉大港(Chittagong)外海的巴桑切爾(Bhasan Char)無人島上。島上的荒涼跟草率的態度讓人權觀察猛烈抨擊,認為孟加拉政府根本無心解決問題。
過了一年,什麼都沒有改變
緬甸政府拒不認錯、國際社會無法給予實質的制裁,再加上孟加拉政府漫不經心與社會的歧視。在迫害過了一年後,各方面的發展對於羅興亞人苦難的改變,並不大。
採訪的最後幾天,採訪團隊遇上了孟加拉的季風暴雨,間歇性的下雨讓難民營內到處都是大面積的積水與泥濘,讓採訪難度增加。趁著雨停我們深入以往不曾進入的營區拍照、探勘。「你們來這拍照有許可嗎?」一位穿著綠色格子襯衫的羅興亞大叔表情嚴肅地質問我們。腳上套著一般羅興亞人負擔不起的高筒黑色雨鞋,雙臂在胸前交岔,不友善的態度讓我們感到畏懼。「有啦!有啦!」敷衍幾下後,帶著不安的情緒我們離開了他的視線。
就在我們在爛泥地裡被跑來跑去的羅興亞小孩包圍時,這位不友善的大叔又出現在我們身邊。這次,我直接跟他打招呼,握了手並報上名字,開始閒聊起來。原來,他是這個羅興亞難民營區中的村長。發現我們是新聞團隊後,他帶我們在村子裡走來晃去,一副我們交情很深的樣子,並且大小聲的要求村民配合攝影,氣勢十足。
要帶我們出營區之前,他在一個轉角停了下來,開始跟我們用簡單的英文講述他逃離緬甸時的遭遇:「村子85個人死掉。小孩子、被丟到火焰裡。房子、焚燒、槍擊、軍人….」他的妻子也遭到波及,在醫院躺了一段時間。
過了一年,這些記憶對他來說仍然歷歷在目。
哽咽、眼筐濕紅,情緒激動。這位原本在幾十分鐘前還架勢十足、要求我們證明自己身份的羅興亞村長,談到過去慘不忍睹的回憶,在外國人的面前落下眼淚。他什麼都沒有了,剩下村長這個稱謂。當外國人來到他的村子拍照時,藉由這個頭銜,他想找回自己失去已久尊嚴。
除了過往的回憶像鬼魅般糾纏之外,難民營內的現況也讓他們感到失落。來到孟加拉幾次後,我們越來越常在採訪的日常中聽到孟加拉人歧視羅興亞難民的談話。但相反的,大多數的羅興亞人提到孟加拉都表示感激,認為他們虧欠孟加拉太多,而這位村長也是其中之一。
寄人籬下,再有怨、也要吞下去。
我們互相道別之後,看著他遠去的背影,漸漸消失在這一百萬人口的難民營中。面對世界的殘酷與自己的無能為力,很難想像他要如何撐下去。現在只過了一年,羅興亞人到底還要再等幾年,才能得到你我都有的基本人權呢?
相關連結:
被連根拔除的民族:當緬甸佛教徒愛上了羅興亞穆斯林,一個羅興亞家族的真實故事
「我們不要錢,也不要孟加拉的幫助,只要緬甸政府把人權還給我們」被連根拔除的民族:一個羅興亞家族的真實故事